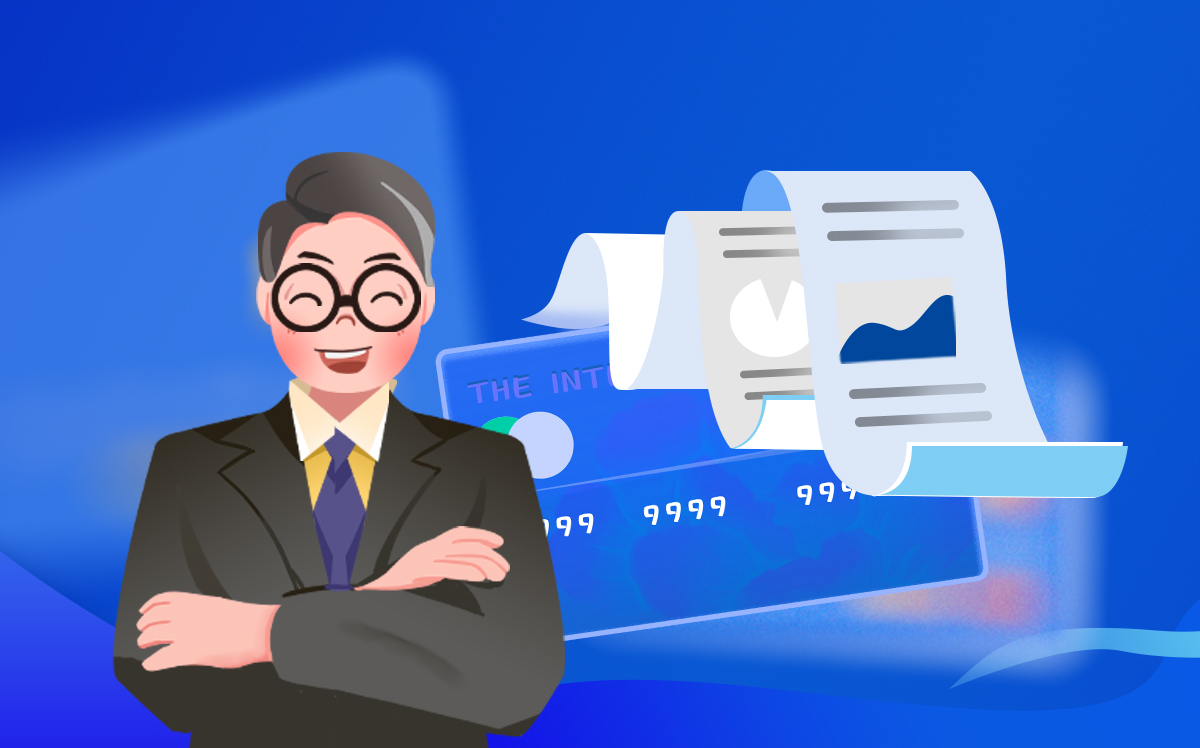環球微速訊:將社會危險性量化評估融入刑事檢察聽證
□建立一種可操作性強的、科學的社會危險性量化評估模型,并兼采辦案人員補充矯正的定性評估方法,應是我國社會危險性評估改革的發展方向。
□將社會危險性量化評估融入檢察聽證制度,是對檢察聽證實踐問題的一種應對路徑,也是對制度本身的補充發展。社會危險性量化評估的適用,可為檢察人員提供一種行之有效的程序化科學評估工具,幫助其開闊視野、打開思路、避免單一思維的局限性。此外,還可為檢察聽證中聽證員或非專業人員充分了解案情提供科學可信的法律材料,從而提升檢察聽證本身以及檢察機關的公信力。
社會危險性的本質是一種風險存在的可能性。就刑事訴訟領域而言,刑事訴訟法第81條第1款列舉了具有社會危險性的五種情形,根據規定內容可知,這五種情形都是對犯罪嫌疑人行為的一種風險評估,大體分為兩類:一類是可能會妨礙刑事訴訟順利進行的;另一類是有繼續犯罪以致危害他人或社會可能性的。因此,社會危險性評估,是對犯罪嫌疑人妨礙訴訟順利進行或者繼續違法犯罪的可能性進行評估。社會危險性評估機制就是將影響社會危險性的各種因素及其影響力進行量化,按照一定的規則對量化結果進行綜合評估,繼而得出犯罪嫌疑人是否有逮捕必要的結論。
 (資料圖)
(資料圖)
域外關于社會危險性評估的研究與實踐
社會危險性評估在司法實踐中已經應用發展多年,時至今日,社會危險性評估已經遍布刑事司法領域的各個階段。
社會危險性評估之所以迅速發展,主要有三大原因:一是法律現實主義與循證實踐的發展;二是降低過高的審前羈押率的現實需求;三是科學技術的發展。
隨著法律現實主義思想以及循證刑事司法的不斷發展,芝加哥大學社會學家歐尼斯特·伯吉斯開發了首個風險評估工具,即利用罪犯的社會經濟特征等因素來預測其再次犯罪的風險。隨后,加拿大提出“風險、需求和回應性”原則和犯因性“八大要素”。其中,“風險原則”就是強調通過有效的風險評估對犯罪嫌疑人乃至社區矯正對象進行區分。犯因性“八大要素”,包括犯罪史、傾向犯罪的態度、不良交往關系、反社會人格、家庭婚姻問題、工作學習情況、藥物濫用和休閑娛樂,這也是現行社會危險性評估的核心指標體系。美國也迅速發展出在刑事司法實踐中應用的多種風險評估模型,包括美國肯塔基州的公眾安全風險評估系統、美國聯邦審前風險評估工具以及以替代懲罰為目標的懲教管理分析系統。據統計,當前世界范圍內有超過200種風險評估工具被用于刑事司法和司法精神病領域風險評估。
當前,國外社會危險性評估的發展主要集中在北美地區,其中,加拿大聚焦于風險評估工具的發展,美國則注重司法實踐中各種風險評估具體應用的有效性。以“再犯危險”為評價對象的風險評估,西方犯罪學界已經開發了四代評估工具:第一代評估工具稱為專業判斷模式,主要依靠懲教人員(緩刑官和監獄工作人員)和臨床專業人員(心理學家、精神病學家和社會工作者)的經驗判斷和專業判斷。第二代評估工具稱為靜態統計風險評估量表,主要通過考察可能引起再犯罪風險的22個因素,給予這些項目定量評分,并將與影響再犯風險有關的因素匯總成風險評估量表。由于該評估工具主要考察靜態的、不可變的歷史性危險因素,依賴犯罪人靜態的過去歷史進行分析,導致存在無法考慮犯罪人員變化情況的缺陷。第三代評估工具稱為風險需求量表,主要包括54項犯因性需求,概括為“八大要素”,并指出這些因素與再犯的相關性與影響。其中除了犯罪史上的項目外,動態的考察因素被用來調查罪犯的現狀和不斷變化的情況。比如,就業情況、新的社交圈、家庭關系等。第四代評估工具稱為整合個案管理和風險需求評估,主要強調對犯罪人的個體化評估。另外,北美現在正在研發的第五代評估工具主要聚焦于能否在第三代、第四代的基礎上增加兩方面內容:一是急性的動態風險因素,包括醉酒或毒癮發作期、失業和社會支持系統崩潰等;二是神經心理方面的風險因素。
目前,北美循證司法實踐中主要運用第四代評估工具,評估涵蓋法庭環節、緩刑和假釋管理以及監獄管理等領域,包括審前的社會調查、假釋委員會決定是否提前釋放以及附哪些條件、監獄通過評估確定安全等級和矯正計劃等。
我國社會危險性量化評估現狀
對于社會危險性評估的研究,學界傾向于建立一種科學的、可操作性強的量化評估機制,以替代辦案人員的主觀審查。我國目前尚未建立起科學、合理的社會危險性量化評估機制,現行法律中有關羈押必要性審查的規定過于籠統,尚無法為司法實踐提供具體、可行的羈押必要性審查指導,從而引發逮捕制度改革中的一系列司法實踐難題。
回顧我國關于逮捕的社會危險性評估改革的三個階段,我國逮捕制度經歷了從對逮捕的社會危險性評估缺乏重視到建立三方構造模式的訴訟化改革,理論界與實務界對“社會危險性條件”的爭議主要源于其較強的抽象性,體現在缺乏客觀化、標準化的社會危險性評估機制。在司法實踐中,社會危險性評估側重于辦案人員的定性評估,難以從系統化的角度客觀評估具體案件中犯罪嫌疑人的社會危險性,影響準確把握是否應予逮捕。因此,建立一種可操作性強的、科學的社會危險性量化評估模型,并兼采辦案人員補充矯正的定性評估方法,應是我國社會危險性評估改革的發展方向。
將社會危險性量化評估融入刑事檢察聽證的必要
檢察聽證作為一種檢察辦案方式,與傳統案件辦理方式相比,具有依法履行監督職責、實現公平正義的法律價值,也有定分止爭、化解社會矛盾的實踐價值,更有提高檢察公信力、促進社會治理的社會價值。公開聽證的過程,既是征求民意的過程,也是對司法活動進行監督的過程,更是貫徹落實“誰執法誰普法”普法責任制的過程,能夠在辦案中及時宣傳法律,提高人民群眾法律意識,從源頭上遏制此類案件的發生。
檢察聽證本身是檢察權的制衡機制,通過聽證程序的抑制、分工、間隔等功能對自由裁量權進行制約,并促進行使自由裁量權的檢察官進行理性選擇。將社會危險性量化評估融入檢察聽證制度,是對檢察聽證實踐問題的一種應對路徑,也是對制度本身的補充發展。社會危險性量化評估的適用,可為檢察人員提供一種行之有效的程序化科學評估工具,幫助其開闊視野、打開思路、避免單一思維的局限性。此外,還可為檢察聽證中聽證員或非專業人員充分了解案情提供科學可信的法律材料,從而提升檢察聽證本身以及檢察機關的公信力。
社會危險性量化評估和刑事檢察聽證制度的融合
域外成功經驗提供了社會危險性評估機制的可行性與必要性的參考。結合前文對域外國家風險評估工具與機制的簡單梳理可見,社會危險性評估隨著法律實證主義與循證實踐的不斷發展,近年來已經成為司法實踐中的前端改革領域。
域外國家不僅使用了多種科學性風險評估工具,而且一直努力將社會危險性量化評估體系化、機制化、法規化,試圖形成司法實踐與立法改革的相互推動。我國的社會危險性量化評估,應該結合我國國情與具體司法實踐經驗,進行本土化的改造完善。一方面,可以借鑒域外國家已有的社會危險性量化評估成果,從法學、社會學、心理學等多重學術視角對風險評估工具進行解析與重構,結合我國國情以及社會特征,辨析我國與域外國家的異同點,從而強化社會危險性量化評估的本土適用。另一方面,可以規劃體系化的社會危險性量化評估機制,在橫向發展完善風險評估工具、形成專業科學的社會危險性量化評估體系時,也應該注重縱向的差異化工具應用,即建立一個全國性評估工具與各地方個性化適用工具相結合的社會危險性量化評估體系。另外,社會危險性量化評估的本土化發展,可以以我國現有的司法實踐數據為基礎,通過新型技術手段搜集司法實踐中辦案人員審查判斷社會危險性的司法經驗,使其更符合我國法律實踐,增強社會危險性評估機制的科學性與有效性。
具體到檢察聽證中,首先按照社會危險性量化評估工具操作,再針對具體案情進行補充性評估,可以幫助辦案人員理清案情、提高辦案效率。同時,也能為聽證員提供一份基于犯罪嫌疑人與案情的清晰、客觀、科學的審查評估報告,幫助其了解案件情況,提供一種社會參與的可行路徑,從而實現檢察聽證制度的高效運行,實現司法實踐中專業性與非專業性的科學有機結合。
(作者為河南省人民檢察院第九檢察部副主任)
責任編輯:hnmd004
- 環球微速訊:將社會危險性量化評估融入刑事2022-09-20
- iPhone14采用高通衛星芯片 得益于高通的x65基帶2022-09-20
- 148元一盒的面膜成本僅10元 敷爾佳毛利率2022-09-20
- 最新工資價位表:什么職業好賺錢?企事業單2022-09-20
- 浙江義烏擬永久性禁售檳榔 約38%的湖南人2022-09-20
- 世界百事通!勞動教育課程實施要下“實”功2022-09-20
- 觀熱點:“老扁擔”挑起鄉村振興新擔當2022-09-20
- 當前時訊:技術創業者于廣平:在艱苦創業中2022-09-20
- 環球滾動:禁捕措施落地見效:休漁禁漁讓江2022-09-20
- 今日看點:「理通三迤」爭“平時”不爭“評2022-09-20
- 天天觀速訊丨中南林科大校長廖小平寄語新生2022-09-20
- 環球消息!“口袋公園”提升句容市民幸福指2022-09-20
- 國媽921口碑母嬰囤貨節,備受關注的嬰兒奶2022-09-19
- 天天熱推薦:有驚無險!幸好有他們!2022-09-19
- 當前熱門:用愛澆灌用心育人——記沈陽大學2022-09-19
- 全球熱推薦:正式通車!蘭州新區白銀市25分2022-09-19
- 環球報道:「你好·南昌」2022.9.19星期一2022-09-19
- 弗爾萊葆董事長周映希出席寵物產業科技創新2022-09-19
- 卓爾數科告訴你美妝品牌要不要搭建私域流量2022-09-19
- 動態:追光|去山野間,磨礪身心2022-09-19
- 全球報道:浙江昨天新增本土陽性1例2022-09-19
- 世界信息:建議取消高新區灑水車早上作業2022-09-19
- 世界熱消息:陽光首院小區消防隱患不整改2022-09-19
- 天天要聞:福學路40-43號樓前路燈建議盡快2022-09-19
- 環球快資訊:榜首!杰瑞入圍山東民企高端裝2022-09-19
- 今亮點!交警支隊召開黨委(擴大)會專題安2022-09-19
- 微頭條丨泗陽法院召開“司法警務規范提升任2022-09-19
- 當前信息:炕煙從此不再是苦差事2022-09-19
- 世界熱點評!江西啟動省級Ⅳ級救災應急響應2022-09-19
- 全球新動態:阿左旗“人才小院”智囊團為鄉2022-09-19